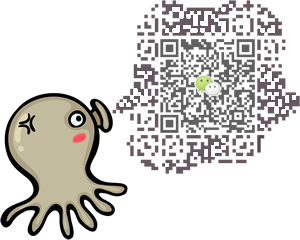80后的集体回忆,你家里还有这些老物件么?
屋子里有两个大红木柜,笨重的,漆橙色的油,带着杨木的纹络,像是有生命一般,会呼吸,吸收阳光、饭菜的香味、我们的笑声与哭闹声,呼出暖暖的颜色与气味,那是生活的光合作用,再神奇不过。

“你妈刚嫁过来的时候,就跟那柜子一般高。”爸爸伸出手掌,笑呵呵地揶揄妈妈。妈妈白他一眼,眼神里竟然也全是笑意,有着暖暖的橙色光芒。

柜顶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破旧的茶叶罐,绿色的油漆被岁月剥落,裸露出红色的铁锈,但上面会有迎客松,依然可见全貌,挺拔俊秀。那是我们的存蓄罐,小心翼翼地把打酱油剩下的一毛钱放进去,每个十分钟扮开盖子瞧一瞧,生怕被弟弟偷了去。也放别的东西,路上捡来的漂亮玻璃块、从书本上剪下来的仙女的画像、半截蜡笔、半块带着奇异香味的橡皮……那些不值钱的东西,对于孩子的我来说如获至宝,可是那么真爱,最后还是藏着藏着,丢了。丢在浩浩荡荡的遗忘之中,不可避免。

一台巨大的收音机牢牢占据着柜子的一角。那个陈旧的录音机是一个亲戚不要了送给我家的,却是我的宝贝,买不起磁带,我就到处借。朋友家所有的磁带我都借来听过,孟姜女哭长城,千古绝唱,舞女泪,长相忆,吻和泪,美酒加咖啡,忘情水,爱拼才会赢……其实现在想来,小学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懂歌曲里曲折缠绵的爱恨情仇,只是娱乐节目如此稀缺的年代,听那个神秘的盒子放出如此细腻的声音,本身就是一种乐趣。

杨木柜左边,是一个小小的橱柜,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调料盒,柜子里铺着不知哪里要来的泛黄旧报纸,放着碗筷还有醋壶酱油壶等,最多加一小袋梅花牌味精。当时吃的醋和酱油都是我或者弟弟拿着一个塑料瓶子到供销社打的,我常常在回来的路上偷着吃醋,一点一点,含在嘴里吧唧个没完。那时候的醋纯粮食酿制,酸甜酸甜的,没有零食的童年,醋也是美味的。回到家,少了小半瓶,难免挨骂,但乐此不疲。醋壶酱油壶是和碗一样的白色瓷器,上面有蓝色字样“醋”“酱”。农村人舍不得丢掉任何东西,脏了擦一擦,一用就是十几年。不像现在这么方便,买一瓶酱油浪费一个瓶子。那些瓶瓶罐罐,被妈妈的手无数次擦拭、轻抚,泛着温柔的岁月光泽。可惜现在我们使用的东西,还没来得及被时间上色,已经被太过方便的生活丢弃。

我经常蹬着小板凳,爬上柜子玩,可是柜子上的暖壶却不敢碰。暖壶里的水永远是滚烫的,那是妈妈在火炉上烧好的。来了客人,用暖壶里的热水泡茶。天寒地冻的夜晚,家里来客了,爸爸会用暖壶里的热水烫二锅头。我们喜欢用暖壶的热水冲白糖红糖。北方漫长的冬天,妈妈用它灌满了一个又一个暖水袋,放在被我们姊妹三个的被窝里,暖和了一个又一个冬夜。现在有了各种热水器,可是依然钟情暖壶,觉得壶里的水满满的,心才安,它尽力地保持着心里的热,是一个物件对人类难得的情谊。有时,就算天很冷,就算人很孤独,从暖壶里倒一杯水,水是热的,用手捧着,也就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。

炕头上是妈妈叠的整整齐齐的被子,棉花细胞了阳光,柔软如云,一针一线都是妈妈亲手缝好的。初冬的阳光像装在簸箕里,越过窗户倾泻下来,泼在炕上,画出一片长方形,像一块发亮的地毯。就是在这一方阳光中,妈妈摆弄这她的针线筐,拍打着蓬松洁白的棉花,为我们缝制过冬的棉裤、棉袄、棉鞋。我坐在她身旁,数着花棉布上大朵大朵的牡丹花,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,咪呜一声,跳上我的膝盖,很快,它就在阳光中睡得香甜 了。


被面是普通的印花纯棉布,平易近人,越睡越柔软。在阳光下晒过之后,它总是牢牢抓着阳光的味道,让人晚上一亲近它,就觉得温暖舒适。其实这布土气又俗气,现在很多人都不用了,可是我却不能割舍,因为这是烙在记忆里的东西,从习惯不知不觉变成了成爱。每次回老家不自觉会选择这样的被子,因为想要重温与它肌肤之亲的那些时光。是呵,因为我就是睡在它上面长大的。

靠下的墙上是我和姐姐的涂鸦,窗台上是我们从学校偷回来的粉笔头。再往上,便是墙上五彩斑斓的画,那是爸爸妈妈专门请画师用油漆画上去的,有繁盛的牡丹、灵动的小鸟、翠绿的树木、粼粼波光的湖水……我特别喜欢拿着一支粉笔沿着图案轻轻描绘,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也能画出那么美丽的画。其实长大了再看,那画实在简单粗糙了,可承载了我孩童时代最斑斓的梦。

红色砖头铺的地,每天洒水清扫,但还是灰蒙蒙的。地上随便扔着两个丑陋的木板凳,被屁股磨得光滑闪亮,冬天妈妈会给板凳穿上自己缝制的“棉背心”。妈妈做饭的时候,我们姐妹三轮流坐在上面拉风箱,爸爸则喜欢坐在上面吃饭。

地上有一个铁架子,架子上放着一盒香皂,一个印着喜字的大红铁盆,那是爸爸妈妈结婚时买的。经常在清晨舀一盆冰凉的水,捧起一瓢泼向顶着眼屎的脸,瞬间清醒,随便用毛巾擦一擦脸,抓起书包就往学校跑。

院子里有两间凉房,随便放点农具,或者柴禾、炭。夏天爸爸磊几块砖头搭个木板制作一张简单的床,我和姐姐特别喜欢在那张床上午睡,还会在泥糊的墙上用粉笔画画。我喜欢放在凉房的那些农具,锄头、木梨,喜欢抚摸那一柄柄被爷爷、爸爸们的老茧磨得发亮的木质把子。那是岁月的痕迹,是勤劳的力证,是人类和土地最为恒久的联系。

门窗是木制的,刷上蓝色或红色的漆。也许是木质不好吧,那漆掉得厉害。只记得过年的时候贴春联,去年褪了色的春联粘着褪了色的漆,一起在风中飘摆。

院子里必定有一两株树,夏天树叶在风中很温柔的摇,沙沙的响。我们在树下嬉戏玩耍,妈妈在树下摘菜、洗衣服,洗干净了就晾在两棵树直接的晾衣绳上。当然,我们也会在两棵树上栓上用自行车带子剪的皮筋跳皮筋。狗窝就在树的旁边,不过从来不拴,我家的狗特自由,跟着妈妈爸爸去野地撒野,晚上去学校接我回家。羊圈和鸡窝挨着,每天晚上羊群归圈的时候,真得是鸡飞狗跳,妈妈站在院子里大声呼喊,不知道喊羊还是喊鸡。

我总是在梦中回到童年,回到老家,回到向日葵开得热烈的那个夏日,回到那个低矮简单却生机勃勃的农家小院。那个农家小院,有牛羊鸡兔和花草树木的浸润,有孩童的欢笑老人的呼喊,因有人气的浸润,所有有声有色,也有滋有味。每天早上第一道阳光照在它的窗口,每天傍晚第一缕饭香溢出,喜怒哀乐岁月漫长,一面墙一个角落一张桌一把椅都跟人一起活着,经过这样的院子,你能察觉它的体温与表情。

现在看见这样的小院子,就会痴痴念念,想要走进去,摸摸羊的头,抱一抱温顺的猫,搂一搂高大的狗,仿佛走进去,就会邂逅一个遗失许久的童年。


本文转自:80后记忆(http://www.80hjy.com/)
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moyublog.com/essay/906.html
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moyublog.com/essay/906.html
加入我们:微信:搜索“Moyu-Blog”
版权声明:本文采用[BY-NC-SA]协议进行授权,如无特别说明,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!